2000万种回家的姿态——关注川籍农民工春运
记者手记
熊筱伟:随着交通体系完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工兄弟的春运回家路,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波澜不惊”。但在静谧的表面下,城镇化这只巨大的手,正掀起他们内心“波涛汹涌”的巨浪。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他们思想变革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陈岩:他们写诗、他们自驾、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农民工的私人记录,颠覆了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网上、报纸上、杂志上,他们的丰富性往往被“讨薪”、“泥腿子”,以及扛着编织袋赶火车的身影所掩盖。今年,我们通过他们的视角看他们的经历,剥离了过分的关怀,还原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真实存在。
李欣忆:2月7日一早,富顺县农民工陈春给我发来一张机场拍的照片,配了几个字:“我好激动。”还在睡梦中的我,以为他是因为第一次坐飞机激动。谁知不久他又发来一条信息:“看见飞机上‘四川航空’没?离家几年好久没见到‘四川’两个字了!”那一刻我明白,身在异乡的游子,身处外地的农民工,他们心中“四川”二字的分量。
吴璟: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背上行囊,即使奔波,即使坎坷,也会冲破一切阻力,回家。
王爽:我采访的农民工兄弟,刚把工作地从成都移到北京。在未来若干年,他都将在春运中踏上千里归途。对于他,成都近若家门。为了梦想与责任远行,这份勇气与担当,让人感到沉甸甸的。
张岚:我的采访对象,一年一度,春节前从新疆回四川,春节后从四川到新疆,如此往返,已是第14年。他满载着父亲爱喝的伊犁老窖和母亲爱吃的新疆红枣,归心似箭,一路奔驰,都是因为“路再远,也要回家”。
赵若言:虽然不曾谋面,但36岁的简阳农民工高雨群跟我在电话里聊起天来,总是热情大方,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但这样的乐观却被独自留在家乡读书的女儿的一条抒发心情的网络留言瞬间打败。我突然明白,不管多乐观的农民工,远离亲人,都是埋在他们心里最深的悲伤。
李龙俊:对于依靠土地刨食的农民,爷爷辈、父辈、子孙的生活往往是不断循环的勤耕苦作。然而近30年,日子巨变,进城成了主旋律。回家的路,城好进,家难归,自己已变,家乡已变,曾经的老家只在梦里。
王成栋:春运年复一年,参与的人叫苦不迭却已经习以为常,围观的人于心不忍却也见怪不怪。春运何时结束?我是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集中流动何时才能结束?答案,或许就是采访时一位农民工兄弟的自问:为啥子我会成为农民工?

四川有2000多万农民工。每到春节,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不同的家乡。
2000万农民工应该有2000万种回家的姿态。每个农民工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在建筑工地干搬运,在百货商场干销售,也可能在玩具厂里当工人,在广告公司当策划。他们不应该被记录为一群面目相似的“候鸟”。
他们可能坐火车回家,也可能乘飞机,还可能自驾小轿车、摩托车或是自行车。他们的归途,不应该被概括为一场为期40天的春运。
他们中有的觉得回家路很艰辛,也有的在路上幸福地看风景。他们的心情不应该被刷上同样的颜色。
我们选择了他们中的21位。21条充满艰辛与梦想的平凡之路,每一条都值得聚焦和尊敬。
我们无意挖掘人在囧途似的曲折故事,只希望记录他们和往年一样的默默行走。我们把这称之为“技艺”,它不是技巧和能力,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或忍耐。
我们无意渲染旅途中的悲情,只希望聆听他们回家途中的一句叮嘱或是一声叹息。我们把这称之为“责任”,它无关品质,可能只是一种本能或无奈。
我们无意描绘美好的前景,只希望和他们像朋友一样聊聊生活、聊聊明天。但他们的“盘算”,可能将汇聚成历史的潮流,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未来。
历史潮流曾将“农民”和“工”混搭在了一起,用“身份”画出一个特殊的“圆圈”,标签出农民工特殊的形象,与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生活方式统统无关。但从2000万乃至2亿农民工回家的足音中,我们分明听到新的历史潮流正滚滚而来。
让身份的归身份,让职业的归职业吧。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政策的精准。对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偏见的纠正。对农民工而言,这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职业荣耀的追求可以得兼。
回家三部曲之一——回家的技艺
谢戴伟说话做事总是慢条斯理,象2月5号那天一样的快节奏,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多见。
这天,是谢戴伟从打工地深圳启程回自贡老家的日子。按计划,他要从深圳坐大巴到广州转火车。
早上9点半,猛地从床上跳起——迟了,该9点出发。他似乎并不紧张,出发前还特意给行李拍了照:一个装了几包零食的塑料袋,一个装了两三件换洗衣服的背包。10点,在工厂宿舍门外拦了一辆大巴上去。
睡过头只是意外的开始。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大巴司机把大家都赶下了车。意识到自己上了黑车后,他“熟练”地配合车上的“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下车步行、换乘破面的进城等一系列“规定”动作,准时抵达火车站。
谢戴伟只买到一张站票。不过他花30块钱买了些熟食,在餐车坐了下来。40多个小时后安全到家。
这是一段娴熟的回家的技艺。历经多次锻炼,他对春节回家的各个环节已经烂熟于胸。即使中间出点小岔子,也总能轻松化解。
对四川2000多万农民工来说,这恐怕是一项基本技能。凭着这项技能,他们熟练地行走在回家的道路上,往返于他们并不熟悉的城市和逐渐疏离的乡村之间。凭着这项技能,他们在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异间像钟摆一样徘徊。
看
习惯于用城市的眼光看农村,用农村的眼光看城市。这种视角,注定了他们的纠结
像广州人一样吐槽 像石桥村人一样聊天
达州农民工汤作勇,36岁,制衣厂工人。
至少在2月6日早上6点12分以前,他觉得此次回家之旅是愉快的:车厢里位置虽坐满了,但人不算多,还是比较松活。
6点12分,起身去打开水泡面。乘务员告诉他9点钟才有。一直等到10点过,还是没有。
此后他不停地吐槽一路上的“这里”和“那里”:烧的开水一会儿就没了,我们厂里可是24小时供应热水;餐厅的饭比我们厂里的难吃得多……仿佛此行的目的地不是达州石桥铺村,而是广州。
8日早上7点,火车驶入达州火车站。下车后,汤作勇打了一辆出租车。师傅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提醒他,前几天有个女人边走边打手机,被人抢了,掏手机出来打要小心。“在广州那边走夜路,非常安心啊!这边真的不行。”汤作勇颇有些自豪地说。
没有直接回家,先赶去看发烧住院的侄女;按老礼,给去世的老人上坟,“让他们晓得我们回来了”。
不少亲戚朋友来串门,让汤作勇感叹,还是这里好啊。去年妈妈心脏病发,卧床不起。原来关系并不热络的邻居,都来母亲床边看望。来不了的,也会托人带来问候。而老婆在广州住院6天,平日里耍得好的同事,却宁愿打牌,也没来看一眼。
说话间,汤作勇下意识地打开手机,刷微博,“这里网络太不稳定了,一条新闻都刷不出来。”
20岁的达州农民工万正伟在回家路上整整“失联”了10小时,“临到家时手机没电了,到家了居然停电?!啥信息都发不出”。一大早就在村里转,他发现了老家的“进步”:路都是水泥路了,两边好多新房子,好多人家还牵了网线。
回家的路上,未来岳母来电催了几遍。都回家两三天了,万正伟还没抽出时间去,“办酒席的人太多,吃都吃不赢。广东那边就不这样。”
吃
最基本的需求,折射出农民工群体性格中最真实的变化与坚守
像城里人一样挣钱 像农村人一样花钱
内江农民工廖联锋出发前特意取了点钱。卡是广东的,回家取钱手续费很贵。
今年是廖联锋在中山市打工的第19个年头。以往都是坐火车回家,这回他和老婆商量要“奢侈”一把——坐长途大巴。火车票一个人260元,汽车票却要610元,一趟下来两个人要多开销700元。
廖联锋觉得大巴啥都方便,就是吃饭没火车方便。2月4号下午4点25分,大巴第一次停车让乘客吃饭,停车场有小贩叫卖盒饭,生意好得很。30块一份的盒饭,太贵了。去年才20!第一次坐长途大巴的廖联锋刻意观察了一下,车上乘客吃和不吃盒饭的各占一半。廖联锋和老婆也觉得贵,还是决定吃干粮,明天再吃炒菜。
5号凌晨1点46分,大巴第二次停靠服务区。廖联锋下车给老婆买了一份盒饭,给自己泡了一盒方便面。盒饭是饭管饱,菜不少,有土豆、红萝卜、白菜、豆腐、血旺。他总结,一是贵,二是全素,“还是必须要吃,不吃身上会很冷。外面又下雨了。”
廖联锋是一家毛衣厂的工艺师,月薪7000元,老婆收入也不低。舍不得买盒饭,是因为节约惯了,这30元在镇上都可以炒3个菜了。
不过他对坐大巴多花的钱似乎并不在意,“确实更舒服些。位子宽,椅背也可以放下去,软座,有洗手间,上车也不用拼命挤。”
南充农民工涂秀娟也是坐的长途大巴回家。这个南充女孩儿喜欢用繁体字记录旅途见闻。
她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司机和一个老乡在车上吵了一架,因为老乡在车上吃零食。司机说普通话,老乡说四川话,两人的争执在旁观者看来难免觉得有些喜剧。她有自己的看法:长途跋涉难免肚子饿,吃点东西填饱肚子无可厚非,同时也要爱护车里的清洁卫生,在不影响环境和别人的情况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便无人会干涉,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行
期待的生活方式与现实的赶路体验,让归途五味杂陈
像电视里一样自驾 像物流一样日夜兼程
2月4日晚上8点,万正伟把行李绑在面包车车顶。电视里看到的自驾游都是这样——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看不同风景。
车是借老乡的,开销远比火车贵;从广东佛山回老家,全程超过1600公里……这些困难,都挡不住万正伟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好心情。晚上8点30分,他更新了自己的QQ签名——“车渐渐远去,祝自己一路顺风”。
深夜11点10分,车行至清远市,天降大雨。万正伟没有停车休息,他和另一位弟兄商量,两人晚上换着开。
第二天上午9点50分,面包车到达主跨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湖南矮寨大桥。他们做了旅途中最长的一次停留——1个小时。大家都把头探出桥外,从离地330米的高空向下张望。“自驾就是安逸,风景好就(多)看看,坐大巴、火车就没法了。”
万正伟兴致很高,自拍了好多张。照片里的他,双手悠闲地插在兜里,斜靠在别人的小轿车上。美中不足的是,和出发时相比,他脸色黝黑。万正伟解释:不停开车,累;车上暖风系统灰尘太厚,又不想费时间清洗。
照完相,继续一路狂奔,万正伟终于在凌晨时分到家。倒头睡了14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5日凌晨5点30分,南充市农民工张果到达武汉火车站。8小时前,他乘坐的列车从湖南长沙开出,现在将在武汉停留4个半小时。
张果买的硬座票,一晚上就“眯了一小会儿”,浑身困软。但他还是抓紧时间下了车,在车站里给家里买了当地特产周黑鸭,到武汉长江大桥逛了一圈,吃了碗热干面。热干面糊嘴,不好吃。但“长江大桥在早晨出太阳的时候,好漂亮。”
比张果起得更早的,是从新疆驾车回家的杨俊。2月4日清晨6点12分,他已经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为汽车除雪了。零下20度,有多冷?他说不远处的博斯腾湖结冰了,冰层太厚,可以跑拖拉机。此时,杨俊连续3天开车,已行驶了近3000公里。
“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工地上跑的人来说,起早贪黑不是事儿。”杨俊放下除雪铲拿起手机,迎着天边耀眼的旭日,一连拍了7张照片。“不是回家(的话),平时很难有心思看日出。”他觉得这久违的日出,真美!
回家三部曲之二——回家的责任
“你晓得个屁!”在手机里,南充市农民工张果对妻子发了脾气。这是2月7日晚上7点,他在成都,离家约250公里。
俩人意见不合。张果临时决定在成都多待一天,见朋友,而一年没见的妻子坚决不同意。“我还不想回切蛮?会朋友还不是想找一下,(看)明年有没得啥子可以做的活路。”他说,家里经济负担太重,年过八旬的奶奶需要供养,娃儿又还在读书。
亲情的期盼、收入的压力,是张果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这些责任有如反方向的巨大拉力,撕裂着张果和他背后的2000万四川农民工脑中,对传统“责任”观念的认知,拖拽着他们为尽一份责,在城乡之间奔波往返。
致子女
“是孩子重要还是挣钱重要?远离家乡,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以后会不会后悔?”
——资阳市农民工高雨群
离开子女挣钱,还是守着子女“穷活”
2月5日下午6点30分,汽车驶入广西境内。晕车反应严重、瘫软在后座里的资阳市农民工高雨群,用手机浏览到女儿的QQ说说——“心情很差,却还傻傻的笑”。高雨群的心像被狠狠抽了一下,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她心情不好是因为考试考得不好,笑是因为我们要回家了。”
高雨群今年36岁,和老公在广州市打工。女儿则留在简阳市读高一。夫妻俩每月能挣8000元,要省下一半作为女儿的教育基金。去年过完年,返回广东没几天,接到女儿班主任电话,说孩子情绪不好,成绩下滑很快。高雨群立马停职赶回简阳,陪了女儿3个月,直到她顺利升入高中实验班。
她发现,没有父母的慰藉,女儿很脆弱。通电话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女儿,常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哭诉同学都是“学霸”,哭诉自己无法排解的压力。可真要陪着女儿,高雨群又做不到。供女儿上大学,至少得要10万元,不外出打工就供不起。在广州上学?“娃儿只能上农民工学校,太撇了!”
思来想去,无法两全。
就在同一天,达州市农民工王海接到老家儿子、女儿的几通电话,“爸爸、爸爸,你好久拢?”这时王海搭乘的老板小车,正堵在高速路上。他说,自己好想早点回去,但每年都要遇到堵车。
“说实话,光顾到挣钱不得行。”王海说,自己和老婆此前都在深圳,娃儿交给爷爷奶奶——他们能照顾到孩子们不饿、不冷,但宠爱得不得了,“奶奶说不准干啥子,娃儿根本就不怕得。”
王海和老婆商量,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于是乎,他老婆回来了,在家附近超市找了工作。钱少了一半,但能照顾家。
致父母
“在外打拼的民工,盼望又害怕春节的到来。盼,是因为只有春节返乡,才能与家人团聚;怕的是,春节后离乡的难舍难分,揪人泪下。”
——德阳市农民工杨俊富
“父母在,不远游”,却不得不远走
“父母在,不远游。”说起父母近况,1982年出生的广安市农民工刘刚,口中冷不丁蹦出这句古训。
2月9日中午12点,刘刚一下飞机就径直乘大巴赶往广安市花桥镇。2013年,他在那儿为父母购买了三室一厅的新居,90平方米。
刘刚小时候父母并未离乡,这让他和父母关系亲密——直到他离家打工,才少于联系。如今,父母都年过六旬,腿脚开始出毛病,又不愿到陌生的广州。刘刚担心他们有个三长两短,就在镇上贷款买了房,一来方便就医,二来过几年他回乡,也能住在镇上。
如今,情况有了变化。刘刚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5岁,快到上学的年纪。一打听,镇上小学不错,中学升学率却极低。他和妻子商量,要到市里读书,就到市里买房——超过镇上一倍的房价,让他打消了买大房子,将父母接来的念头。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是不得不游,只有尽量(离父母)近一点。”作为月薪7000元的某刊物编辑,80后刘刚本想将父母照顾得更好一些,却被老一辈农民工杨俊富的诗歌言中,“仍然步着我们的后尘。”
和刘刚一样,内江市农民工付华平春运目的地,也是父亲家——不过,她是带着母亲一起回家。自打她儿子出生,父母就过上“异地分居”的日子:父亲在老家帮大女儿带娃儿,母亲则远奔深圳,为二女儿付华平带儿子。付华平是农民工子弟校的教师,没有钱雇保姆。
她发现,父亲打来的电话越来越频繁,找母亲聊些家长里短。母亲接完电话,有时会躲在角落里偷偷抹泪。说起这些,付华平觉得愧疚、难过、心疼。
今年回家,付华平专程给老爷子买了超过3000块钱的外套、毛衣。春节后,让母亲向父亲道别,跟着她返回深圳,这句话像一根刺,卡在她喉咙里说不出来。
致伴侣
“我不想要农村里老辈子指手画脚的相亲,我想要不粗鲁、体贴人的你。但问题是,你在哪里?”
——南充市农民工涂秀娟
带着城里人的婚姻观,参加农村传统的相亲
“已是‘剩斗士’的我回家过年,相亲的尴尬在所难免。”
2月8日早上9点,刚刚坐上回乡的大巴车,南充市农民工涂秀娟就在微信上吐槽。这种不快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冒出了“不想回去”的念头。
涂秀娟今年28岁,在广东省清远市一家耐克鞋代工厂当文员。长相清秀的她外出打工5年,没有男朋友。
这急坏了老家父母。连续几年春节回家,都为她张罗了走马灯式的农村相亲:约定时间、地点,双方亲戚10多人出马,齐刷刷瞪着俩年轻人交谈,还不时七嘴八舌地插话。这让涂秀娟觉得没有一点隐私,很尴尬。长辈在场,年轻人只好“演戏”,“(相亲时)都话不多,看上去都很老实、很靠谱。”她说,只有单独相处,才真正知道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就像韩剧里演的那样。
“老辈子指手画脚,只看老不老实、工作靠不靠谱,至于身材好不好、性格粗鲁不、体不体贴人,根本不考虑。”涂秀娟不停抱怨相亲“陋习”,可一回到家,也没拒绝父母安排的相亲。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涂秀娟内向而腼腆,平日最大乐趣,是躲在屋里绣十字绣、贴钻石画。她说,平时在厂里,不怎么接触男同事。
王波比涂秀娟早回来2天,这位眉山市农民工是遵照父母要求,提前回老家摆酒请客的。半年前,他早已和南充来的女朋友偷偷领证结婚了。
和涂秀娟一样,王波也看不惯村里人热衷的“传统”相亲——不同的是,他成功逃脱了。如今的妻子,是在攀枝花读大学时认识的,“想法、爱好,能说到一堆,就结婚了。”偷偷领证,是因为家里不同意,觉得找本地人才长久。
赶在春节前回家摆30桌酒席,就是想弥补自己的决定和老家传统观念的“裂缝”。“买肉买菜、通知亲属、摆桌子……要我自己说,弄死都不请客。”
回家三部曲之三——回家的盘算
“老实说,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35岁的眉山人熊建勇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说这称呼否定了这些年来他的努力。2月9日,熊建勇乘坐包机抵达成都。在他看来,自己是衣锦还乡。他乘坐的是温州企业和政府全资包下的“农民工专机”。
过去的8年,他不断地学习知识和积累人脉,调整自己的工作心态,让自己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满足”。
熊建勇的生活已经和城里人没有区别,但是农村的户籍、城市的工作,总有那么一点错位,总能在不经意间又触碰到敏感的神经。他的潜意识里,有对自己的身份解读。在不断的碰撞、撕裂中,熊建勇说,乡村已经渐行渐远,城市梦想已逐渐实现,一切都在慢慢过去。
职业认同
根在农村,荣耀在城市
[ 对话熊建勇 ]
记者:这次回家探亲,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吧?
熊建勇:纠正一下,我不是回家探亲哦,这是休年假,10天,加上春节放假7天。
记者:这有什么差别么?
熊建勇:回家探亲,听着就好像专门在说农民工。我现在是销售经理,年薪15万(元),一样的要加班、出差、应酬。像三险一金这些,城里人该有的我都有。我不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有啥子好大差异。我们厂里的几个大学生也就是(我)这样子,不能说他们也是农民工吧?
来温州8年,熊建勇终于“爬上”了温州某按摩椅生产厂的管理层。年前,熊建勇买了房子,把妻子、女儿都接到温州生活,去年又买了车子。如今,夫妇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女儿已经入读温州一家知名幼儿园。
然而他对先前的遭遇仍耿耿于怀——刚来浙江打工的时候,别个一看就喊他“农民工”,有的还说些怪话。他觉得,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 对话冷辉 ]
记者:对现在工作满意吗?
冷辉:我现在也算小有成就吧,在鞋厂里也算个中层干部,年收入嘛,也还是有15万以上。
记者:关于工作,给农民工兄弟一点建议吧。
冷辉:我只有小学文化,但我喜欢弄技术,一年365天,大概300天以上在跟技术打交道。现在能混口饭吃,靠的还是不断积累经验。
冷辉今年才29岁。听记者夸他年轻有为,这位德阳市农民工连连称谢。
2月7日早上飞机在成都落地,下午冷辉就和几个朋友聚了一下。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的他,感觉当年的小伙伴变化好大——有的继续读书,有的早早结婚,有的仍在外闯荡。他说,自己现在的成就在朋友间算是中等偏上。小时候成绩很好的一个男同学,高考没考好,出来打工,现在28岁了还单身,说很羡慕我。“其实,我倒更羡慕你,不像我,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客气的语调,掩饰不住冷辉的自豪。
职业规划
停下脚步,提升职业技能
[ 对话张果 ]
记者:你过完春节就要赶着出门?
张果:不急,我准备去县里的农民工培训班报个名,学下室内装修。
记者:以前培训过吗?为什么要去培训?
张果:没有(培训过)。我是搞(室内)装修的,以前工人少,是我们挑别个,谁给的工钱多给谁干;现在(工人多了)是别个挑我们,谁干得好让谁干。
去年冬天,张果过得有点“不安逸”:在长沙市区飘荡了三个月,挣到的钱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更恼火的是,春节后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而跟自己一起打工的广西小伙,“活路多得做不赢,一个月收入一万多都很轻松”。
和广西工友比,他觉着自己技术确实不过硬,“脑壳里没得货”。这让张果下定决心,宁愿少挣一个月钱,也要让自己拥有“金刚钻”。他在家乡报了班,学一个月的室内装修课程。“学会了,活拉得多,钱也就挣得回来。”
[ 对话田小龙 ]
记者:在外面过得习惯吗?
田小龙:不出去才不习惯,只是有些活路搞不来,(因为)没得多少文化。
记者:那你以后有哪些打算?
田小龙:现在学点东西还来得及,我现在做五金,打算在里面学一两年,攒点钱、学点技术,出来开个店。
田小龙说,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28岁的达州农民工有个刚刚五岁的儿子,简直是个“花钱机器”,每学期七八千元的生活费用让他有点吃不消。看见以前五金厂的同事纷纷自己当老板,做起了五金生意,好的一年能挣20万元。这让他动了心思。
他盘算着,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客源、资金,也初步掌握了一点技术。他说,近期会在厂里继续储备资源,“希望两年以后,(自己)这个店能在成都或者达州开起!”
职业需求
不光挣钱,更要让自己的本事有用武之地
[ 对话陈春 ]
记者:满意自己的工作吗?
陈春:我觉得自己被放错位置,没有得到认可。
记者:那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让你满意?
陈春:能发挥自己在技校学过的食品包装特长就行,当然离家近一点更好。
自贡市农民工陈春,强调自己的“用武之地”,说现在工作单位(食品厂)对他并不尊重。学食品包装出身的他,“什么食品,咋个包装我都晓得一些”,但拿出自己方案,却总会被否定,尽管事后证明他是对的。
他认为厂里不重视知识,管理太粗放。过完年,他要去成都周边的食品厂看看,找寻自己的“用武之地”。
[ 对话涂秀娟 ]
记者:对工作满意吗?
涂秀娟:不满意。
记者: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你满意?
涂秀娟:我理想中(的工作),要有一定自由性,希望能自己安排时间,而不是被别人安排。
涂秀娟是广东某鞋厂的办公室文员,这位28岁的南充市农民工没有像父辈那样,“能挣钱就忍了”。她明确表示,决定改变现状。过完春节,要去朋友在成都开的店,给她做帮手。
现在供职的工厂,有什么不好?涂秀娟看重环境、氛围——厂里很少有人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做事的方式很粗暴;一天的生活,也就是限于在电脑上“噼噼啪啪”,制作ppt、工人教材、组织活动……都是杂事。而去朋友的店,时间自由度大,朋友对她也更倚重。虽然在创业期,前景不定,但涂秀娟说,为了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她宁愿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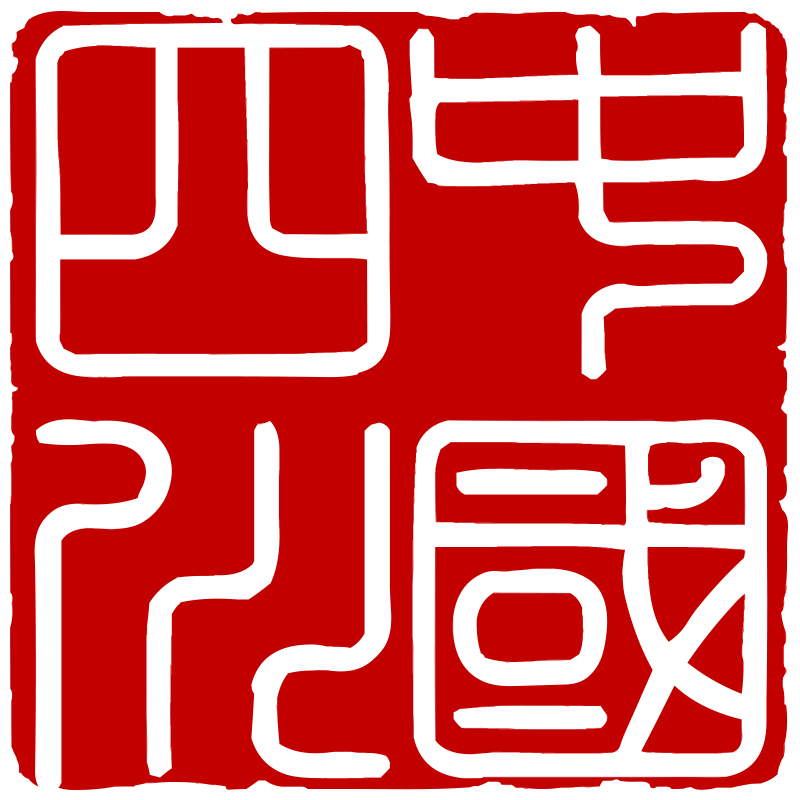











 微信
微信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

 头条号
头条号

